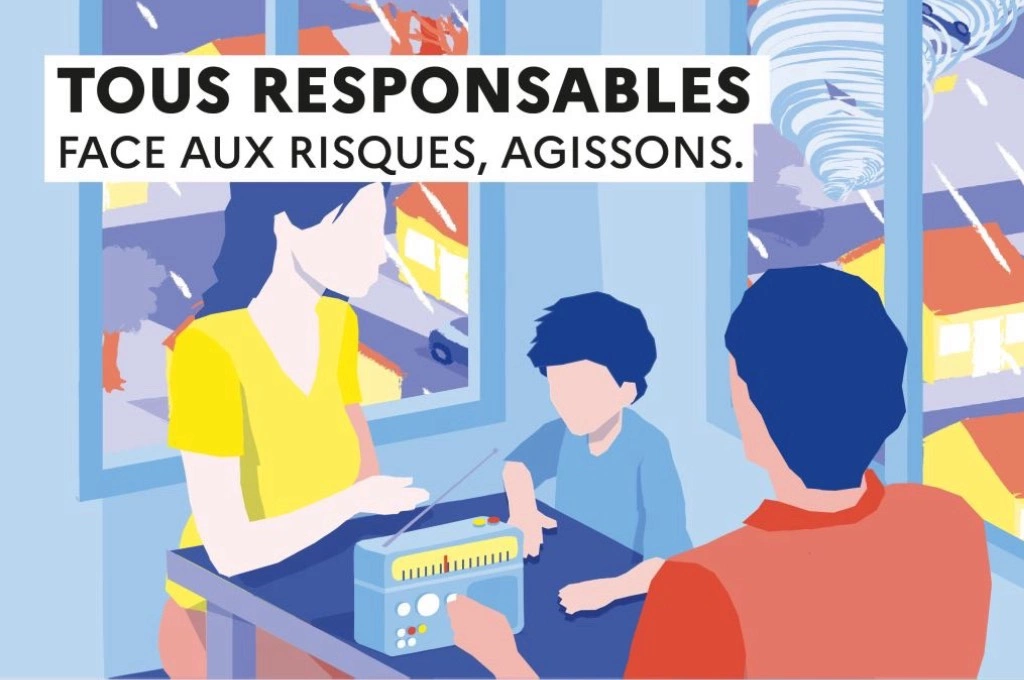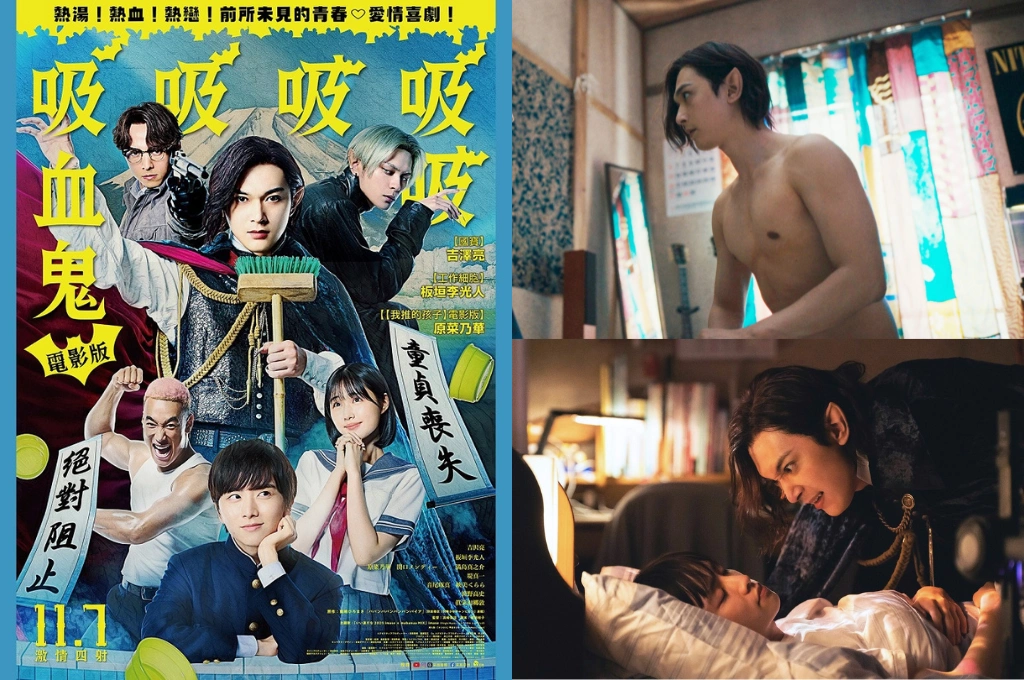少年站在鏡子前皺緊眉頭,指尖比劃出一把手槍,動作俐落地上膛,然後直指前方——那一刻,彷彿是對準螢幕外的觀眾開槍。

《恨》劇照
這正是《恨》令人難忘的片段之一,也象徵著電影中壓抑、憤怒與暴力的爆發點。透過黑白影像,它直面階級與族群衝突,帶領觀眾近距離凝視一座城市的怒火與絕望。
巴黎街頭點燃的青春怒火
《恨》(La Haine)以九○年代巴黎郊區為背景,寫實呈現城市邊緣青年在種族歧視、警民衝突與社會失衡中的掙扎。故事聚焦三位來自不同族裔的年輕人,包括猶太裔的文茲(文森·卡索 飾)、阿拉伯裔的賽德與非洲裔的烏貝。
這群少年生活在巴黎十八區,幫派林立、警民對立等陰影如影隨形。某日,在一次鎮暴行動中,文茲的好友被警方重擊送醫,文茲在憤怒之下,意外撿到一把遺落的警槍,決心「以暴制暴」討回正義。 《恨》劇照
《恨》劇照
值得注意的是,電影的設定中僅以一天的時間跨度,與觀眾一同深入逐漸升溫的社會緊張與個人情緒,以黑白色調紀錄街頭少年如何以槍聲劃破沉默,發洩焦躁與不安,鏡頭深刻捕捉青少年的憤怒、迷惘,以及法國社會無法遮掩的裂痕。
電影背後的真實事件,兩個少年的悲劇啟示
《恨》(La Haine)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僅在於它對法國郊區青年的細膩刻劃,更在於它受到兩宗震驚全國的真實事件啟發。 《恨》劇照
《恨》劇照
1986年12月6日,22歲的法籍阿爾及利亞裔學生馬利克·烏塞金(Malik Oussekine)在巴黎拉丁區的街頭,遭到警方追捕並在一棟建築物的門廳內被毆打致死。當時,他並未參與任何抗議活動,只是恰巧經過正在鎮壓學生示威的現場。
七年後的1993年,17歲的扎伊爾裔少年馬科梅·姆博沃萊(Makomé M'Bowolé)因涉嫌竊盜被逮捕,並被帶至巴黎第18區的警察局。在拘留期間,警官帕斯卡爾·康潘(Pascal Compain)為了恐嚇他認罪,將槍對準姆博沃萊的頭部,結果意外走火,子彈近距離射入姆博沃萊的頭部,少年當場喪命。
這兩起事件皆引發民眾強烈抗議,尤其後者更在巴黎市區掀起連續數日的騷亂,也法國社會不得不正視警察暴力與種族歧視的深層問題,也成為導演馬修.卡索維茲(Mathieu Kassovitz)創作電影的靈感。
巴黎才沒有你想像中的浪漫  《艾蜜莉的異想世界》劇照
《艾蜜莉的異想世界》劇照
在《艾蜜莉的異想世界》中,害羞又充滿想像力的艾蜜莉穿梭於蒙馬特的巷弄間,與神祕男子的展開甜蜜邂逅;而在《午夜巴黎》中,伍迪·艾倫筆下的城市則是文學與藝術的夢境,夜幕低垂時,主角搭上復古汽車,回到海明威與費茲傑羅的年代,巴黎成為浪漫與懷舊的代名詞。 《午夜巴黎》劇照
《午夜巴黎》劇照
然而,這些影像所描繪的巴黎,僅是城市的一面。在電影《恨》(La Haine)中,鏡頭轉向巴黎郊區的93省,展現了移民社區的現實:高失業率、種族歧視、警民衝突,揭示了法國社會中移民與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困境。
法國政府長期以來強調「色盲」政策,避免在官方統計中涉及種族分類,試圖營造一種平等的國家形象。然而,現實中,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的移民後代在教育、就業和住房等方面仍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巴黎郊區的移民社區常被視為「問題地區」,公共設施落後,教育資源匱乏,導致社會融合困難。  《恨》劇照
《恨》劇照
電影獲頒坎城榮耀 成影迷心中不朽經典
《恨》(La Haine)自1995年上映以來,已成為法國電影史上無法忽視的經典。卡索維茲憑藉此片榮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電影則在法國本土吸引超過200萬名觀眾,成為當年度票房前十的國片之一。2024年,電影更被改編為嘻哈音樂劇在巴黎首演,以全新的面貌詮釋法國仍然存在的種族歧視、警民衝突議題。
卡索維茲
《恨》不僅在影評界獲得高度讚譽,還引發了政治層面的關注。時任法國總理阿蘭·居貝(Alain Juppé)要求內閣成員觀看此片,並表示儘管對片中反警察的主題有所保留,但認為這是一部能讓人更了解現實的電影作品。
除此之外,《恨》也對法國電影產業產生了深遠影響,開啟了以郊區(banlieue)為背景的電影潮流。例如,導演拉德‧利(Ladj Ly)2019年的作品《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便刻劃了巴黎郊區的警民衝突和社會不公。
《恨》不只是九〇年代法國電影的經典,更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藝術創作與社會思考。它的黑白影像與剪接節奏,至今看來仍充滿實驗性與張力;片中對警察暴力、階級衝突與邊緣青年處境的描繪,更在社運圈、文學界與藝術院校中被視為不可忽視的存在。
《恨》將於5月29日在臺灣重映,不論你是第一次接觸,還是多年後重溫,都值得走進戲院,在大銀幕上感受那股狂躁的青春、與世界對抗的叛逆精神。
(圖片來源:好威映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