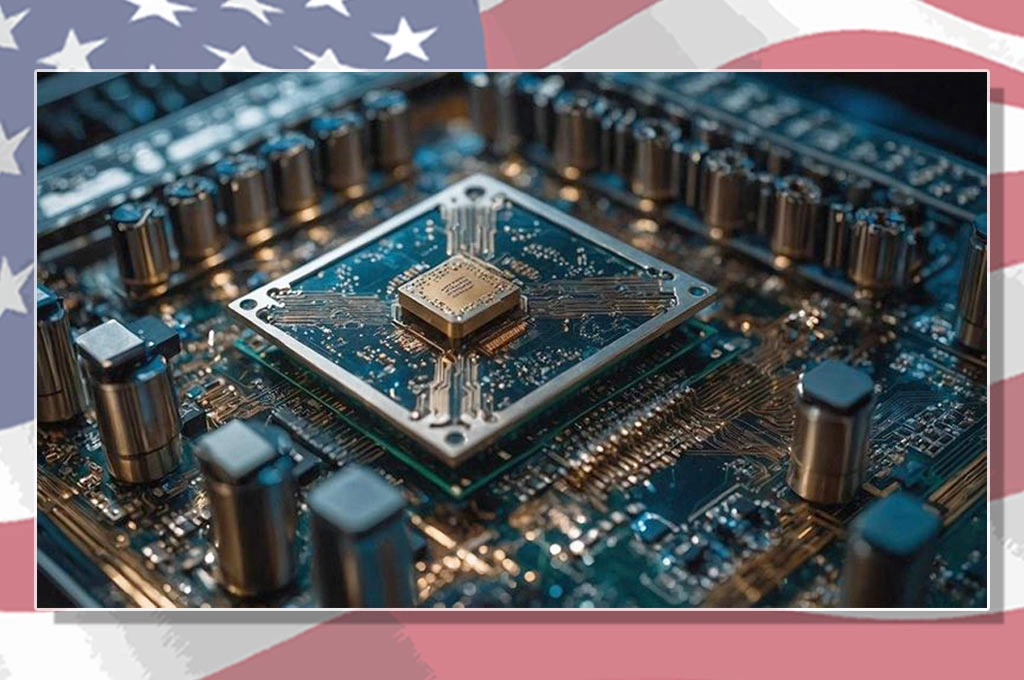蕭菊貞的敘事裡,奇蹟是「賭」出來的。當然,賭並非盲目,也是經過細緻的評估、審慎的決斷,只是到底會不會成功,決策時並不知道。很多人以為政治的決斷都是真知灼見、預知未來,但其實,真正的決策,通常都是在無知之幕下進行,總還帶有點風險、一點未知,和隨時都有的變數。
學生時代看過蔡崇隆的紀錄片《奇蹟背後》,講RCA和台灣的一段恩怨糾葛,政府選了一批優異的工程師到美國RCA總公司學新技術,RCA來到桃園投資生產收音機,招收了許多生產線女工。命運的交叉就此展開,學成回台的男子工程師們成為半導體產業的教父級人物,而在地的女工卻因為污染與工殤,一生與病痛相為伍。片名叫《奇蹟背後》,奇蹟就是映襯,重點在背後的工殤和污染,以及為此付出代價的無名女工們。
但我也從此記得,那段政府遴派工程師赴美學習,奠定台灣半導體產業基礎的故事,胡定華、楊丁元、史欽泰、曹興誠,這些名字被記了起來,後來我有幸在很多很多場合,比如審查工研院預算時,比如爭執晶圓代工赴中投資要不要開放時,遇到這些紀錄片裡的傳奇人物,並從旁觀察他們彼此間的交鋒。
從政策賭局到站上國際頂端 《造山者》述台灣半導體奇蹟
幾日前看了蕭菊貞的紀錄片《造山者》,不同於蔡崇隆的敘事,蕭菊貞以赴美學習的工程師們為主線,談的是奇蹟本身。奇蹟是怎麼來的呢?蕭菊貞的敘事裡,奇蹟是「賭」出來的。當然,賭並非盲目,也是經過細緻的評估、審慎的決斷,只是到底會不會成功,決策時並不知道。很多人以為政治的決斷都是真知灼見、預知未來,但其實,真正的決策,通常都是在無知之幕下進行,總還帶有點風險、一點未知,和隨時都有的變數。
反正就是拚了,黨國不分、一黨獨大的時代,行政院長和經濟部長等一干人,在南陽街上退輔會開的豆漿店做了決定,派工程師去美國學習半導體,然後就浩浩蕩蕩的去了,到底會不會成功,不知道。這些年輕工程師們拚命地學,不放過任何一分鐘,連假日出去玩,都要提心吊膽珍惜生命,因為國家產業的興亡都在你一人肩上。現在好難想像這種使命感,但訪問起當年的九傑,他們提起都還會掉淚。
後來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了,竹科發展起來,半導體、晶圓成為一項產業,大家都說住在那兒的工程師是新貴,意思是很賺錢。再後來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了,產業因為全球化趨勢故,開始為了是否西進中國爭執不休,最後政策從「戒急用忍」轉向了「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大家喜歡說只有開放,其實沒有管理,但故事再往下翻一頁,就會發現管理不僅有,而且還很重要。
中國崛起,國家補貼下以雄厚的資金打破市場的價格,量產、低價、偷技術,把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弄得天翻地覆,管理卻還是有的,最新技術沒有移動、面對併購堅定不移,產業比的是氣長,不是眼前的利益。十年苦撐,產業還在,世界卻又變了一個樣,美中打起貿易戰、科技戰,供應鏈被迫重組,免稅的紅利正在消失,全球公認的半導體教父在公開演講中宣稱「全球化已經結束了」。
而蕭菊貞還在拍,她這部《造山者》拍了好久,本來是要說歷史,結果卻被瞬息萬變的產業趨勢和政治變局攪亂了節奏,台灣也因為這波地緣政治的變化,忽然被推上了科技戰和貿易戰的浪尖。當年的有為青年都老了,半導體成就了國家興旺,也成就了他們各自的人生;作為輔線的部分,蕭菊貞也訪了奇蹟背後土地被徵收的人們、在生產線上工作的女工們,不能否認,沒有他們,只有精英的話,這座山也是造不成。但科技戰、貿易戰風風火火,雖然紀錄片顧及了那些面向,卻也不敵局勢變化下產業的上上下下、高低起伏。
《造山者》圓恩師遺願 生涯半導體始終相隨
試映的時候本來沒有想太多,就是半導體的紀錄片,結果開始沒多久就說是清大社會系的教授吳泉源的遺願,讓我深受震動。雖說對科技社會學那類的領域不很興趣,但當年帶著我認識社會學的老師,吳泉源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讓我認識在社會學裡面,「理論」談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大議題,而不是我所熟悉的政治學當中的理性選擇、博弈理論。我也還記得是他帶著我們唸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解開常識上對「看不見的手」不講道德的誤解。
我聽吳泉源講半導體紀錄片這件事也好幾次,倒是沒想到完成這件事的是蕭菊貞。他訪問的學者們,很多是我的同輩、甚至後輩,師出吳門的研究者。影片當中有胡定華的告別式,我也看見很照顧我的藝文界前輩邱再興先生伉儷出席追思的畫面,想起邱先生也跟我提過他早年參與半導體的風雲。隨著敘事展開,蔡英文的畫面也跟著出現,勾起我對當年這場紀念會的回憶,印象中也是因為總統一時忙不過來,才拜託陳副總統出席。
我也想起在政府服務的期間,半導體一直是跟這段旅程糾纏不休的議題。每一年的資訊月、台北電腦展是差不多時間,也要接見訪台的電腦展大咖和台裔工程師。最重要的是電腦展那篇稿子,得用英文寫。寫的人固然不是我,但作為把稿子送出去的人,也總是要承受那對稿子不滿意的「第一擊」。
常常是在公車上、在捷運裡、甚至家門對面的便利商店當中,接到不滿意的電話。那端會叫我去問誰問誰,然後就是一個先寫中文,再找人改寫(不能是翻譯)成英文,然後字斟句酌、反覆修改的歷程,通常完成的時間是出席日的早上七點半,我也經常在送小孩上學途中接到再做修改的指令而為了小孩穿鞋太慢、忘記帶水壺之類的事而氣急敗壞。
一個一個的會議,談半導體學院,談半導體發展,有時候我也會出席,為了避免聽起來都像天方夜譚,特別去買了日本人寫的《圖說半導體》來研究,也總算看得懂那些名詞,什麼是奈米、什麼是DRAM,封裝是什麼意思。造山者創造了山,我則對山裡的礦石又撿又選,精修在精修,用最前現代的方式在改稿的壕溝中組裝成講稿,在重要的會議上講出來,博得滿堂專業者的喝采。仔細一想,半導體離我的生活並不遙遠。看蕭菊貞《造山者》的過程,我也重新審視了一次自己的職業生涯中,關於半導體的種種回憶。
對了,那家「欣欣豆漿店」的歷史現場,在蕭菊貞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追索後,發現後來被改建成一棟補習班,我曾在那裡補過托福,只是留學的夢,因故,始終未圓。
(圖片來源:造山者-世紀的賭注 A Chip Odyssey 臉書;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傅建文)